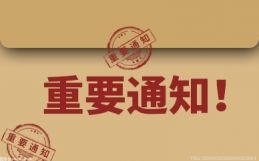俠客島:是該依法重拳治理網絡暴力了_最資訊
言無刀鋒,卻能殺人。
 (相關資料圖)
(相關資料圖)
最近的悲劇新聞大家都知道:武漢一名6歲小學生在校被撞身亡,之后其母楊女士不勝網絡暴力之擾,縱身一跳,離開了人間。
沒想到仍有人“按鍵傷人”,向著孩子父親發出誅心之論:“是老公把她推下去的吧?”“260萬到手,又可以娶個年輕美女了。”
面對如此網絡暴力,確需拿起法律的武器。
(圖源:網絡)
一
網絡暴力,顧名思義,是發生在網絡空間的暴力行為。2022年11月,中央網信辦印發《關于切實加強網絡暴力治理的通知》,其中明確提出:“網絡暴力針對個人集中發布侮辱謾罵、造謠誹謗、侵犯隱私等違法信息及其他不友善信息,侵害他人合法權益,擾亂正常網絡秩序。”
網暴雖表現為一種語言“軟暴力”,卻同樣可以侵犯當事人隱私權、名譽權、財產權,對人造成極大精神傷害。從世紀之初“小小馬哥”“高跟鞋虐貓”“銅須門”等事件中的人肉搜索,到2021年成都49中學生墜樓事件中敵對勢力的造謠煽動,再到部分網民對江歌媽媽“騙取流量”的污蔑誹謗……天下苦網絡暴力久矣。
從立法角度看,中國《民法典》《刑法》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等綜合立法,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《婦女權益保障法》《英雄烈士保護法》等專門立法,最高法、最高檢關于誹謗、侵犯個人信息和侵害人身權益等的司法解釋,都對治理網暴作了相關規定。
從司法層面看,治理網暴今年首次寫入“兩高”報告。最高法工作報告專門提到,去年審理了侵害“兩彈一星”功勛于敏、“雜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等名譽案,讓人格尊嚴免遭網絡暴力侵害;最高檢工作報告也提到,去年“堅決懲治網暴‘按鍵傷人’,從嚴追訴網絡侮辱、誹謗、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1.4萬人。”
能夠看出,實施網暴者不僅無恥、無知地將矛頭對準國家功勛人物,還呈現出“大規模侵權行為”的群體性特征。為何法律有規定、司法有追懲,網絡暴力依然屢禁不止,甚至屢屢造成令人扼腕的悲劇?
二
對此,國家網信辦網絡法治局局長李長喜表示,現有法律法規仍存在針對性不強、銜接不暢、效力不高等問題,制度實施效果與人民群眾期待還有一定差距。
與代表社會法益的意識形態范疇的侮辱言論案件,或誹謗、侮辱國家執法機關人員的言論案件相比,在干預涉及純粹私人法益的網絡暴力方面,目前法律展現的力度有限。
這一點,從警察權介入的主動性,和檢察機關公訴頻率就能看出差距。比如“取快遞女子被造謠出軌案”,雖然最終法院宣判網暴者入獄,但在辦理該案之初,警方手段仍限于批評教育、雙方和解,造謠者只愿口頭道歉,不愿賠償受害人的經濟損失,甚至稱受害人“獅子大開口”。可以說,由于法治觀念和權利意識淡薄,懲治網暴的防線從一開始就失守了。
最近武漢這位母親則沒那么幸運。對他們而言,精準查找、定位加害者并非易事。網絡無遠弗屆,加害者可能遍及全國甚至身居海外,若沒有相應機構和機制及時介入,想僅憑個人力量收集、存儲、讀取海量證據,相當困難。
還有一個難點:網絡暴力一旦構成針對公民個人的誹謗犯罪,就不歸公安機關管轄,需要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。到這一步,“取證難”的受害人又將面臨“證明難”的境地。如武漢墜亡母親一樣,從刑法證據鏈條證明網暴與母親自殺的因果關系,殊為不易。即便能證明存在確定因果鏈,由于網暴主體眾多,責任分散,很容易陷入“法不責眾”、不了了之的境地。
(圖源:視覺中國)
三
還有許多網友在討論平臺的責任。在網暴事件中,平臺該做些什么?
《關于切實加強網絡暴力治理的通知》指出,平臺要通過內容識別預警等措施,建立健全網暴預警預防機制,如設置一鍵防護功能等,強化網暴當事人保護;同時,要分類處置網暴相關賬號,依法從嚴處置處罰網絡暴力。
從這些措施看,即便是永久禁言某些賬號,仍難免“按下葫蘆浮起瓢”。加害者也許換個馬甲,就能繼續信口雌黃。
應該說,這是事后監管必然導致的問題。目前,我國法律要求網絡平臺采取“通知—刪除”規則履行監管義務,只有發現侵權信息后,平臺才能采取措施,防止傳播行為擴大;只有明知或應知網暴行為發生、不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暴力行為發生,或暴力后果擴大時,平臺才會承擔相關法律責任。
某種程度上,“事后”意味著“滯后”。從實踐看,平臺的滯后性刪除難以彌補網絡暴力已經造成的傷害,甚至有一些平臺在逐利天性和流量思維的邏輯下,還熱衷推送刺激性、情緒性、煽動性內容,對履行監管責任并不積極。
如何扭轉這一局面?可行路徑是,各類平臺必須有效貫徹《關于切實加強網絡暴力治理的通知》要求,根據網暴周期規律,建立事前預防、事中監管、事后追責的全鏈閉環治理機制,尤其從加強內容識別預警、構建網暴技術識別模型、建立涉網暴輿情應急響應機制這三方面,建好預警預防機制。
防治網暴需要形成合力。中國互聯網協會副理事長、清華大學互聯網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曉東提出一條協同管理的路:治理網暴,需從道德、法律、監管、技術等層面發力,政府、行業、平臺、企業等多方參與。
怎么落實?刻不容緩的有兩件事——
一是回歸法治軌道。無論何種形式的“媒體”,不管網上網下、大屏小屏,都不是法外之地、輿論飛地。一段時期以來,既有法學專家呼吁制定防治網絡暴力專項法律規范,也有多位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建議制定反網絡暴力法。如果現有分散立法、修補立法解決不了問題,就應該專門立法、系統立法,提升法律的威懾力量。
二是推動文明上網。表達有邊界,流量有底線,構建良好的網絡生態,文明網民是基本盤。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不想被網暴,就該注重德行、自我約束。匿名和虛擬不是“張口就來”的理由,道德和法治才是“言由心生”的前提。
標簽:
軟件


信用卡逾期不還有什么結果?信用卡逾期怎么辦理停息掛賬?

觀展數文會 感受數字與文化碰撞的魅力

手機
-
三星rv415筆記本怎么調亮度?三星rv415網卡性能參數 2023/04/11
-
信用卡逾期多久協商停息掛賬比較好?貸款逾期解決方式有哪些? 2023/04/10
-
騰訊為什么告老干媽(老干媽和騰訊事件誰贏了) 2023/04/07
-
買理財保險在哪里買好?保險是買好還是不買好? 2023/04/07
-
新債中簽后幾時賣?新債中簽后什么時候賣出合適? 2023/04/07
-
美債上限什么意思?美債上限多少錢? 2023/04/07